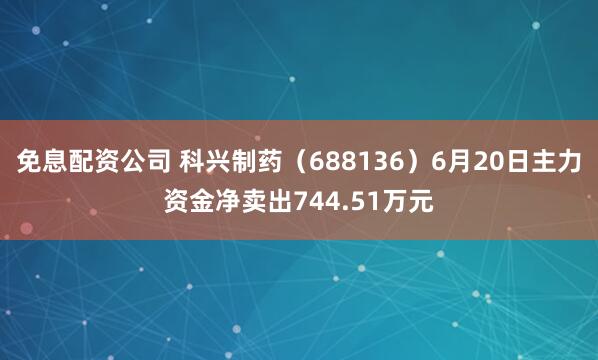1976年,在陕西省临潼县零口镇的一次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件名为利簋的青铜器。这件珍贵文物上的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清晰记载了周武王在甲子日一天之内灭亡商朝的历史事件国内股票配资实盘排名,与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相关描述完全吻合,为这段历史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
根据《尚书》《左传》等古籍记载,商朝之所以在一天之内土崩瓦解,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商纣王的主力部队正在东方征讨东夷部落,导致都城朝歌防御空虚。当周武王率领联军突袭时,纣王仓促间只能临时征调战俘和奴隶组成军队。这些缺乏训练的乌合之众在牧野之战中很快溃败,加上商军内部发生叛乱,最终导致商朝覆灭。这也印证了《左传》中纣克东夷而殒其身的论断。
然而,一个历史谜团随之产生:商朝灭亡后,由攸侯喜统帅的十万精锐大军(实际数量可能只有两万左右)以及林方、人方、虎方等十五万军民,连同他们的竹制船只和物资,突然在历史记载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商丘日报《商文明,永城汉兴之地的文化源头》一文也曾专门探讨过这个未解之谜。
展开剩余80%近代以来,学界对此提出了多种假说。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猜测认为,为躲避周人的追杀,攸侯喜可能率领残部远渡重洋,最终抵达美洲大陆,成为印第安人的一支祖先。这一假说得到了一些佐证:美洲土著中流传着祖先渡海而来的传说;考古发现了一些类似甲骨文的刻符;还出土了其他可能与商文化相关的遗存。不过,这些证据尚不足以形成定论,需要更多权威研究来证实。
近年来,山东地区的考古发现为解开商军去向之谜提供了新线索。关于商朝灭亡的原因,传统史书多归咎于纣王失德,但这种道德评判显然过于简单。实际上,商末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势:内部统治集团分裂、气候异常导致农业减产,以及严峻的军事压力。考古证据显示,纣王当时很可能陷入三线作战的困境:东线要镇压东夷叛乱,西线要应对周人和鬼方部落的威胁。
学者井中伟与王立新的《夏商周考古学》指出,商朝在山西南部沿汾河东岸布置了一系列军事据点,这些呈线状分布的商文化遗址,明显是为了防御来自吕梁山区李家崖文化的鬼方势力。与此同时,甲骨文记载显示,纣王曾多次亲征东夷,如在十月又二,往征夷方、在十月,王来征夷方,在攸侯喜等。李学勤教授通过青铜器铭文考证,还原了商军东征的具体路线:从兖州出发,经新泰、青州,最终抵达潍坊。
在这种形势下,纣王不得不做出战略抉择。历史证明,他选择主攻东线,在西线采取守势,可能还试图利用鬼方与周人互相牵制。这一战略决策也解释了为何纣王会先囚禁周文王后又将其释放——这显然是基于局势变化的理性选择,而非传统史书描述的因谗言或贪图美色等肤浅原因。
上世纪80年代,山东淄博沂源县东里镇发现的东安古城遗址最初被误认为春秋时期的城址。但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这座古城被确认为商代遗址,其历史可追溯至5000年前,城市建制史超过3000年。该城历经商、周、春秋(纪国浮来邑)、战国(齐国盖邑)、秦汉(盖县)、魏晋至隋(东安郡)等多个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东安古城的地理位置极具战略意义:地处交通要道,易守难攻,完全符合古代军事防御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该城恰好位于纣王东征路线的新泰—青州段,且位于本不应出现商代古城的沂蒙山腹地,这一发现令考古学界颇感意外。
更关键的是,东安古城出土了大量商代青铜器,包括饰有兽面纹的铜铙、弓形器等,其形制与殷墟出土的同类器物高度相似。铜铙是古代重要的军事指挥器具,所谓鸣金收兵的金正是指此物。这类贵重军用品在普通遗址中极为罕见,其集中出土暗示这里可能曾驻扎过大规模军队。此外,山东多地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如著名的苏埠屯商墓出土器物)都与殷墟风格相近。
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安古城一带就有人类聚居。到商代时,因其战略位置重要,商人可能在此筑城以控制东夷地区。从出土铜铙等证据来看,这里很可能是纣王东征大军的一个重要驻军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岳洪彬研究员指出,散落在山东各地的商代青铜器,特别是东安古城出土的铜铙,是商王朝主力部队曾驻扎的铁证。这些考古发现表明,商纣王的主力部队很可能就驻扎在山东一带,并未远徙他方。那么,他们的最终结局如何?
《汉书》记载,周成王时期,薄姑氏联合其他四个方国发动叛乱,被周公东征平定。值得注意的是,在纣王死后,这些东部方国为何还敢反抗周王朝?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商朝的主力部队仍驻守在此,为这些方国提供了军事后盾。反过来看,这些残余的商军对新兴的周政权确实构成严重威胁,周公东征将其剿灭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联军作战往往难以形成统一指挥,最终被各个击破也在所难免。
综合各种证据可以推断:纣王死后,征讨东夷的主力部队很可能分散驻扎在山东各地的商属方国境内(从后勤保障角度考虑,单一诸侯国难以供养整支大军)。这些部队最终在周公东征中被歼灭。当然,也不排除有小股商朝遗民渡海远遁的可能性,但这仍有待更多考古发现来证实。
发布于:天津市财盛证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